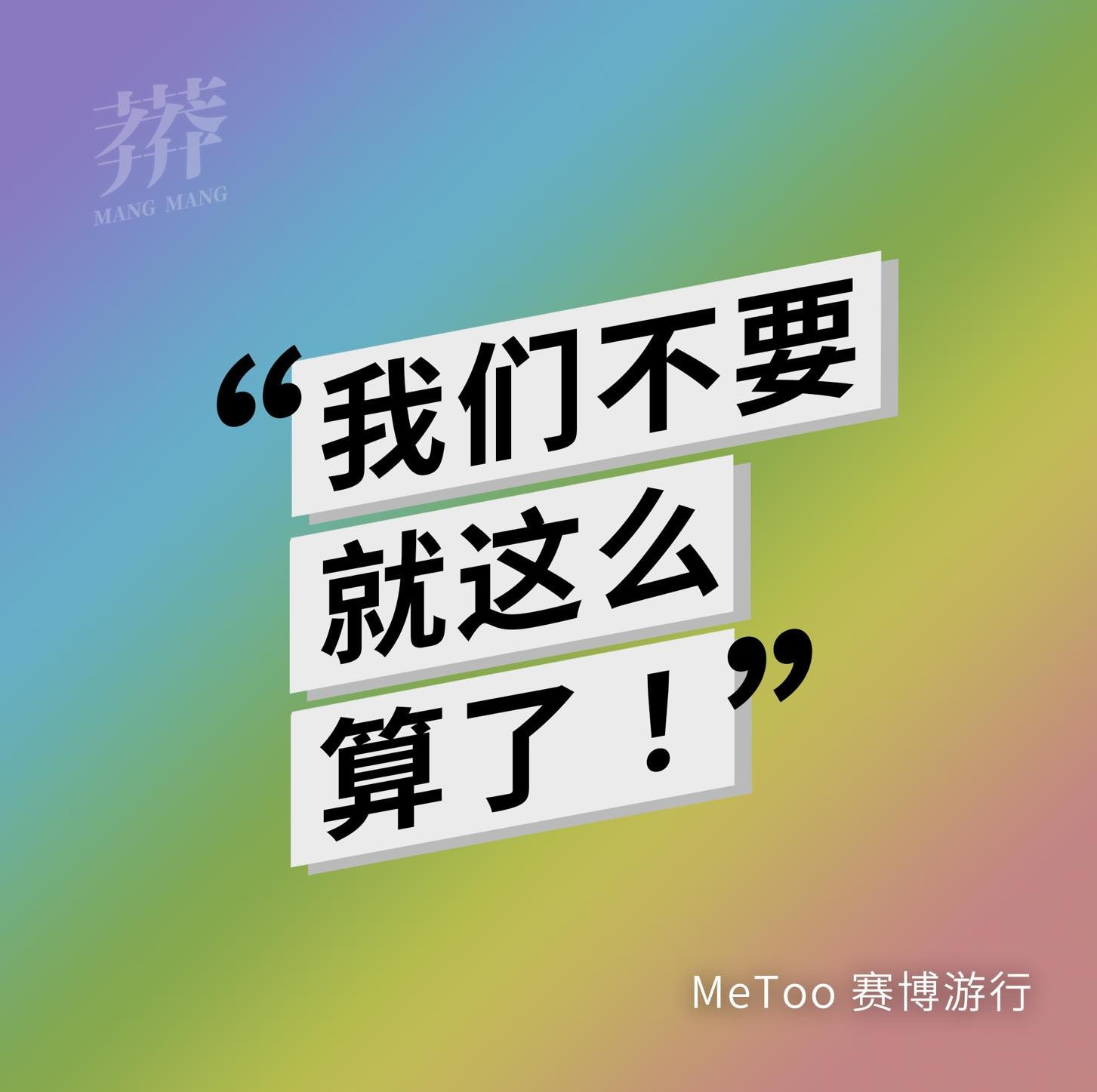#不要算了 | 为了未来的陈述与质问
这是“不要算了”赛博游行中的第一篇自述文。作者讲述了随着年龄增长所经历过的程度不一的性侵犯,对权力不平等和强奸文化做出剖析,发出了具有分量的质问。
这是“不要算了”赛博游行中的第一篇自述文。作者讲述了随着年龄增长所经历过的程度不一的性侵犯,对权力不平等和强奸文化做出剖析,发出了具有分量的质问。
一、
本文将通过我个人从小到大遭遇的事件,来说明我的观点,提出我的质问。陈述事件将会尽量少用比喻的修辞,以客观的第三人的角度来陈述这些事件。然而,在我如此努力想客观、公正地表明我的立场的时候,文化、审查等等对我的强奸就已经开始了。请读者原谅我分不清性侵、强奸、猥亵、性骚扰的区别,它们的区别好像就是“插入”与否,生殖器“露出”与否……吗?我不懂,明明都是对一个人的无情碾压,而法律名词的区分,似乎对受到的伤害也一并区分等级。肉体的痛苦和伤害也许可以区分等级,但是精神的创伤又要怎么区分呢?因此请原谅,不分清几者实在是我没有这项能力。以下的事件,以我成长从小到大为序。
二、
九岁转学第一周,忘记第几天,在班上被一位男同学当众隔着裤子摸了下体,那位男生一边摸一边用方言大声重复喊着:“摸xx,摸xx……”(“xx”是方言里面女性下生殖器的代称)。当然在摸之前,他还亲了我的侧脸。还未下课,老师同学都在,同学哄笑,老师的反应我记不清了,反正没人帮我。我不得已面对这种场景,只记得电视剧里女性遇到这种事情要拼死反抗,那么就能换来周围的同情。于是我当即大声哭泣,以表示我的拒绝。
后来我反应过来,原来我九岁开始,就已经从电视等媒介中明白了女性要誓死保护自己的“贞洁”,我要表明自己是个“正派”的女子,我对于自己的立场有如此大的恐惧。以至于我下意识担心的不是自己被侵犯了,而是周围人要如何看我。而我又有另一个问题:为什么从那么小开始,小学二年级的男生,就知道以生殖器为荣?他们为什么可以冒犯老师的权威?为什么老师都没有来安慰一个九岁的小孩,为什么我身边那么多人、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干预?为什么学校不能保护我?为什么学校不需要教育那个男生?对,后续就是没有后续,他的行为没有后果,而我落下了“玩不起”的评价。
三、
在十一岁的时候,被一个玩得好的男性同学突然压在班里的桌子上,他直接摸到了我的胸。我的想法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,因为担心被扣上“早恋”的帽子。
四、
到了初中,我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形象,希望自己好看。但是在家庭内部,却经常被一位男性长辈嘲笑我“大象腿”。
那位长辈,是一位教政治的初中教师,还是学校的领导。彼时我还不知道原来评价他人的身材,尤其是权力上位者对于下位者,在国外就算是一种性骚扰;更不要提对方是个成年人,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还未满14周岁的孩子。而且在当时的中国教育里面,初中的政治是包括对未成年保护法的科普、以及思想品德教育的啊。那位长辈在外颇受人敬重,还曾经竞选成为了记不清是村级还是镇级的人大代表,但是对于言语上的骚扰却无知得可怕。
五、
还是初中,我加入了学校的学生会。那位长辈找了我部门的部长,了解我的日常,在吃饭的时候找我谈话。他说他去找了我的部长,去询问了他对我的看法。“你知道他是怎么评价你的吗?”他问。我沉默,并不想和他说话。他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,家里其他的人总会帮他接话。他继续说:“他说你跟人相处得好,经常和部门里的人开玩笑,做事挺认真、挺活泼的。跟男同学也相处得不错。”我当时微微松了口气,心想这是个还不错的评价。我觉得他看穿了我的反应,他接着说:“你以为是在说你好话?‘认真’可能是,但是‘活泼’是什么好词吗?”我已经有了不满,说道:“不是吗?”他接着说:“词好不好也要分开看,形容男的也许是,但是形容女生,活泼,外向真的是好词吗?”我隐隐约约察觉了他的意思,用沉默消极对抗。他接着说:“活泼,外向的女生,那是说女生喜欢跟各种人接触,都相处得好,是那种交际花。”末了补充一句:“你还觉得人家在夸你。”
怎么说呢,一个脏字都没有,一个脏话都没有,却什么都说了,他知道,我也知道。“妓女”、“人尽可夫”、“婊子”等等词语,虽然他没有直接说,但是已经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对“活泼”一词的解释,扣在了我头上。后来我知道了权力上位者拥有的解释权的厉害所在——字典的解释、我的解释,都是无用的,他拥有的权力,随时可以否定所有的权威,不存在真理。
六、
从初中到高中,培训班老师带着我们一群人去ktv,他会搂着我们女生,也会开荤段子玩笑。比如:“今晚xx酒店xxx号等你。”
七、
大学,晚上下课9点30,在学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等公交车。马路对面灯火明亮,一堆男生在打篮球,大约三四分钟就有车驶过。本该是很安全的环境,很不巧,我遇上了露阴癖;很不巧,他半脱了裤子在自慰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成年男人的生殖器,我担心他会强奸我,我身体自动发起了冻结反应,等到能动弹的时候,我第一反应是大声尖叫,引起对面打篮球的人的注意,同时不顾一切地朝着对面跑过去,马路上有辆私家车差点撞到了我。到了马路对面,我感觉我是安全的,第一反应是先看看自己穿什么。我穿的是黑色宽松的长T恤、牛仔裤、运动鞋,非常“安全”的装束。
但是,非常“不幸”的是,当时互联网上已经开始有女权博主科普女权主义思想,当时反对的是受害者有罪论。我也非常认同,并且将这类思想拿出来与我朋友分享,我能够在网上为遭遇性侵的女性摇旗呐喊。但是我自己遇上了,我却第一反应、下意识地先检查我的穿着,哪怕我很清楚,我能很理性地说出强奸就是强奸,跟女性穿着什么没有关系,强奸就是犯罪,就是施暴者的错,采取暴力就是错。我很明白,我很清楚,我努力学习了女权思想和逻辑,去读书、讨论、实践。但是当我自己遇到了这种事情,为什么我第一反应还是先查看自己的穿着是否“妥当”呢?我被自己下意识的举动给击垮了,我感觉我的努力似乎都没有用,我本应该最关照我自己的,我怎么还是被奴役我的那些东西所控制呢?
我大哭,哭了许久,痛哭我的无力,痛哭我努力了,却还是逃不开思想的牢笼。当然,好在那之后有我的朋友、同学们,安慰我保护我,让我好好走出了这一事件。
八、
如是,都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。就我的经历而言,虽然施暴者都是男性,但是阻止我说出口的因素中,性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他们是“受欢迎”的人,是男权文化的“被保护者”,受人“敬重”的人,是成年人;受害者的我是未成年人,是“不可信任者”,是“需要严格考核者”,是“无权者”,是“被剥夺者”。我说的话会因为我的很多属性而缺乏可信度。像是点着蜡烛的屋子,烛光充满了整个屋子,但是有一块石头在烛光旁边,连带石头的后面一整块都是黑暗的世界。那块石头的名称叫“权力”,沉重且不可撼动。
所以“性骚扰”的“性”,不是“性别”的“性”,是“性交”的“性”,“性侵”的“性”。它带着它天然的暴力属性而来,它没有戴上锁住它的镣铐,它是凶悍的;无法在现有的字典里找到精确定义,无法用现存的逻辑去与它沟通、抗争——因为它就是由父权逻辑生产出来的。只能自己积蓄力量,等到我自己成年、取得了权力,用权力去威吓这些曾经的施暴者,让他们对我客气,有距离。这是一种力量对力量的威吓。可是我很不明白,为什么不能让伤害从未发生呢?为什么人不能有良知呢?为什么政治课的教师不能深刻学习自己教授的内容呢?如果连课本都是假的,如果连基础教育都是虚假的、不值一信、可以只说不做的,那么我们考取高分努力理解又是为了什么?那么到底是什么建构了我们的认知?为什么我们质疑的声音却总是发不出来呢?
辛柳记于2023年6月27日深夜
(刊文有略微删改)